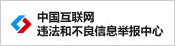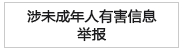昆明暴恐案后的生存震荡商家称警察多了客人少了

“3·01”事件后,全副武装的警察在昆明火车站值勤-杨帆
2014年6月的“中国好人”的候选榜单中,出现了昆明警察和保安的名字,一共5人。3月1日晚,他们在昆明火车站与持刀砍杀无辜者的歹徒搏斗,人们记住了他们危急关头的英勇行为。
昆明还有无数勇敢的人。他们在事件之后重新回归日常,为自己的生计和事业忙碌。火车站周边乃至城市各个角落里,都有民警值守的身影;平静如昔的生活节奏之下,全城戒备。

昆明火车站站前广场上设置了水泥防撞栏,夜晚,没有生意的搬运工坐在上面休息-王中杰

陈宇贵在站前广场候客-郎晓伟

火车站已重归平静。一对情侣在此相拥-王中杰

昆明警方在全城各处都加强了戒备。高考期间,佩枪的民警在云大附中考点执勤-马闪山
“3·01”事件已经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昆明火车站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变化也显而易见。陈宇贵拉客时发现,警察多了,安全感增加了,但拉到的客人却少了。
陈宇贵站在火车站前,四周的灯光将他的脸照得刷白。背靠着不久前新装的防护栏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来往的背包客。但凡有旅客模样的人走过,他总要追上去低低地问一句:“住店不?”对方摆摆手,他便讪讪的退回来,继续观望。
“晚上9点后,这里有几百个拉客的人。”他的一口重庆腔有些沙哑,这是长期熬夜造成的。这种昼伏夜出的生活,他已经过了6年。
这个“拉客仔”有一段不普通的经历,“3·01”事件时,他因为与歹徒对抗,积极帮助伤者,一度得到“平民英雄”的美誉。现在,他与许许多多事件亲历者一样,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前两天,昆明共有5个人进入“中国好人”候选名单,他们分别是“3·01”事件中勇斗歹徒的民警谢启明、王军、王海岗、马维福以及献出生命的保安张建光。
这个活动,陈宇贵并不知道。眼下,他更关心自己拉客的营生。
一
5月28日晚9点半,昆明火车站。这一天,距昆明“3·01”事件已过去近3个月。此时的站前路依旧热闹,卖炸洋芋的、卖卤面的摊点热气腾腾,拉客的电单车骑士们叼着烟,三三两两地坐在车上闲聊。
陈宇贵固定的等客处,是站前路上一排新置的白色围栏,这里紧邻火车站出口。“再往里,警察就不让进了。”
栏杆上,斜倚着形形色色的中年男女。“都是拉客的人,有些还是店老板。”陈宇贵望着出口说。
每当夜色降临,站前路就成了店老板们活跃的舞台。陈宇贵在此拉客6年,对火车站周边的每一个陈设、每一个店主,甚至民警,都再熟悉不过了。这个重庆男人今年51岁。7年前受表妹之托来昆明帮忙看店,才看了一年,店铺转让,他失业了。“看到别人拉客比较自由”,加上年纪大了,他也没回去,待在昆明当起了拉客人。他的老婆和两个已成年的孩子都还在重庆,每隔两三个月,陈宇贵就要回老家看看家人。
其余的时间,他都在火车站周边度过——在站旁租了房,像其他的拉客人一样,与周边旅店老板混熟……
火车站周边的小旅社多由老小区的套房改建,陈设简单,价格便宜。根据房间大小,房价一般分为40、50、60元三个级别。陈宇贵拉到客人,如果与客人谈好40元的房价,带到任何一家周边旅店,他都可以提成10元。当然,他也可以多喊10元,提成20元。
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出门,凌晨三四点钟回家,每晚能挣50-60元,陈宇贵很知足。在“3·01”事件以前,这是一份辛苦却单纯的活计。而事件发生以后,这份拉客生意一落千丈,就连深居简出的旅店老板们也得亲自出来揽客了。“有时候,整晚一个客人也拉不到。”
陈宇贵扫了一眼站前广场上随处可见的警察:“现在,火车站的警察起码有几百人。”他似乎习惯了“几百人”这个量词,不管是否准确。
这是全城戒备的时刻。
二
3月1日晚上,在火车站广场拉客的陈宇贵协助民警,加入到对抗持刀歹徒的队伍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陈宇贵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包括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中,并被冠以“平民英雄”的头衔。
“陈宇贵,当时我也在现场,我也是英雄啊!”5月28日晚上,见又有记者来找陈宇贵,一旁的一位中年男子搂着陈宇贵的脖子,开起了玩笑。
“你别信他,他骗你的。”陈宇贵一本正经地说。性子不急不躁的他每逢受访,总免不了要回忆当晚的惊心动魄。但他的脸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表情,很淡然。
“3·01”事件已经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昆明火车站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变化也显而易见。陈宇贵每晚拉客时,还是穿那件深绿色格子外套,可住宿的客人少了,警察却多了起来。
“现在火车站周围的警察起码有几百人。你看,这些都是新装的。”陈宇贵指了指站前一排排铁围栏,“大概10多天前,广场前装了这些栏杆。现在火车站周边都围了起来,只有一个口可以进。我们拉客的人也只能在外面拉。”
夜里10点,昆明火车站站前广场就像一个大迷宫,那头身姿矫健的金牛被挡在重重的栏杆后,金牛身边,旅客们正从唯一的入口进入,将行李放上安检输送平台。铁栏杆外,多个蓝白相间的水泥墩形成了一堵“城墙”,成为入站的首道屏障。
“这些水泥墩是新疆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后,刚拉来的。”陈宇贵对金牛身边的每位“新客”十分熟悉。
三
重重戒备之下,随着旅游淡季到来,拉客者们感觉到了3月初的那场事件带来的影响。
5月28日,从下午4点站到晚上9点半,陈宇贵没拉到一个客人。敞亮的灯光下,一个微胖、头发随意扎在脑后、穿着一件宽松遮臀短袖装的中年妇女向陈宇贵走了过来。
“陈宇贵,今天咋个样?”妇女操一口纯正的四川话。
“不行啊。”陈宇贵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妇女叫张阿妹,43岁,是火车站旁边一家招待所的老板娘。张阿妹来昆明已有20年,开旅店也有10年的时间。这些年,她的生活圈都以火车站为圆心。“3·01”当夜,张阿妹的旅店保护了一批又一批匆匆赶来避难的人。
看着眼前这片人流如织的地方,她露出了鄙夷的表情:“挺复杂、挺乱的。这里坑蒙拐骗的,欺行霸市的,什么人都有。曾有人想欺负我,不让我开店。我告诉他:‘你是一条命,我也是一条命,我没惹着你,你怎样随便!’”她忿忿地说:“在这个地方,你怕人,就做不走。”
一个月前,深居简出的张阿妹终于也坐不住了,和不少同行一样,她也加入了揽客的队伍中。开旅店10年来,她首次亲自出门揽客。以往,她的客源都来自陈宇贵这些拉客者们。
“客人们的戒备心强了。”陈宇贵总结道,胆小的旅客宁愿晚上在执勤的警察身边打地铺,也不愿住店,这让他颇为烦恼。“以前一天能挣五六十块,现在一天才拉到一两单生意,挣二三十,连房租生活都不够。”陈宇贵说。
张阿妹更愁。她的旅店有29个房间,这些房间都是租来的,每套房每月都有2000元左右的租金。每天人力加房租,本钱都在700元左右。没有客人,就意味着持久的亏损,这也是她不得不出门揽客的原因。
四
55岁的昆明的士司机彭鲲还是像以往一样,穿梭在这个城市的每条道路,包括拉客者们盘踞的火车站。
每次乘客上车,他总习惯问一句:“请问到哪里?”但凡乘客用云南方言跟他说目的地,他马上就转换为昆明口音回答,以此让对方放心,他是识路的。
除非乘客有意攀谈,彭鲲才会与客人聊天。“3·01”以后,外省游客坐他的车,偶尔会问:“街上这么多武警、特警,师傅你怕不怕?”
“我觉得很好,你们放心吧。”彭鲲认为,游客们若真的害怕,就不会来旅游了,“其实他们也就只是问问。”
“现在的治安很好,反而是人的脾气太大,有的动不动就打架。我倒觉得,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人的心态一累,什么都累。”开了20年的出租车,彭鲲从未遭遇抢劫等事件。他习惯了在乘客上车前先仔细观察,因为“要干坏事的人,看神态就能察觉”。
他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他曾拉过3个男乘客,几人上车后要求到昆钢。“两个人不吭气,只有一个人说话,而且不敢看你的眼睛。那时到昆钢最多120元,我开口要300,他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肯定有问题。后来我借口车抛锚让他们下了车。到昆钢的那段路,那几年经常发生出租车被抢的事件……”
“如果恐怖分子坐到我的车上,我直接把他送去派出所。”这个当过兵、参加过两山战役,同时也是“昆明雷锋出租车队队长”的司机说,警察给了城市更多的安全感。“特别是学校门口,现在学生们上学放学时,特警、武警和片区民警都会来执勤,这非常好。坏人见到了,总要避一避。”
“3·01”以后,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是:昆明街头的警察多了,“见警率”提高了。烈日下,他们全副武装站立的笔直身影,让这个城市居住的人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安全感的提升不仅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心态,警察们也感受到了来自群众的善意和关心。
“‘3·01’后,我们全员上岗。中午去吃饭,饭店老板坚持不收我们钱。一刷微信,朋友圈里到处都是餐厅针对警察免单的消息。”每每谈到“3·01”,最让任庆伟难忘的都是这些镜头。他坦言,这种时候,警察的荣誉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就像我们的局长所说:‘我们不干谁来干?公安在这种时候肯定要站出来!’”
任庆伟在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虹山派出所担任巡逻防控中队长。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很长时间——像所有的昆明警察一样,“3·01”事件以后,没有休息过一天。
5月28日晚,陈宇贵正在火车站候客时,任庆伟正在派出所值班巡逻。从当天上午9点到第二天上午9点,上满24小时,再在派出所处理日常工作到下午5点多,他才能回家休息一会儿,手机必须随时保持开机状态。
五
5月中旬,一位昆明民警在微信朋友圈里感叹:“现在每周的状态是1、2、3、4、5、6、7;1、2、3、4、5、6、7……无限循环中……”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来自昆明市公安局巡逻防控支队的数据显示,目前,昆明巡逻防控等级已进入最高级别。全昆明每天投入街面的警力达9058人,比此前常态警力数增加88%。其中,五华、西山、盘龙、官渡、呈贡等主城区的防控警力数为每天5577人,比以前的警力数增加了154%。所有巡逻车全部投入街面防控,巡逻时必须警灯闪烁。
与此同时,除了常规的派出所等一线部门派警力巡逻,机关单位民警也要求各个部门在维持好部门正常工作运转的情况下,每天抽调10%的警力,派遣车辆,配合业务部门上街展开车辆巡逻与徒步巡逻。所有民警全员取消休息。
陈宇贵熟悉火车站大多执勤民警,虽然民警们并不认识他。他甚至有些同情这些警察:“有时候看到流浪的老人,警察会叫我带他们去住店,还自己掏钱帮付住宿费。他们24小时轮班,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辛苦。”
除了日常巡逻防范,自4月30日起,云南警方在全省展开了各种反恐实战演练与培训,一线巡逻民警全员配枪。精度射击、快速反应射击,街头盘查遭遇反抗时如何应对、发现暴徒行凶时如何应对……“真枪实战”的演练让一线民警们感觉到,现在的培训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实用性。
“‘3·01’事件毕竟只是一个突发事件,现在昆明的治安形势是平稳的,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都是好的,市民们可以放心。”如今,任庆伟已习惯了值班配枪,“现在如果值班不带枪,心里肯定会有点忐忑,万一遇到突发事件,武器能第一时间制止犯罪,保证大家安全。”
“我们现在尽职尽责,就是想做好我们能做的。”昆明市公安局巡逻防控支队女警王曦说。“3·01”以后,这个10岁男孩的妈妈抛下家庭,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了20多天。儿子只能由奶奶照顾。
“孩子现在上小学四年级,他肯定不理解。但是,现在我们全局实行的是动中备勤制度,这是为了发生突发状况时,能第一时间集合警力。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六
生意越来越惨淡,张阿妹第一次动了把店盘出去的念头。
这个四川女人在昆明还是有过一段好光景的。那些年,火车站附近的各大客运站还没有搬迁,她的旅店每晚丝毫不愁客源。客运站搬迁后,生意清淡了些,但也从未遇到过现在这样的寒冬。
一个女人在火车站周边独自开旅店是不易的,她叫跑车的丈夫过来陪她。后来,儿子也过来给她帮忙。现在,旅店生意不好,张阿妹开始盘算着让儿子出去打工,甚至首次动了把店转出去的念头。但是,“可能到明年都很难转出去,现在生意难做”。
女人家深夜出来拉客,张阿妹承认,心里有些害怕。“出来时还是会四处看。害怕也没办法,一家人还要生活啊!”
多年在火车站旁淘生活,张阿妹早已适应了这个地方的鱼龙混杂。人们惯常于戴着有色眼镜看火车站周边的旅店,总认为这些地方是抢、骗、色横行之所。
张阿妹并未否认这点。“到我店里住宿的,六成以上的单身男客都有过在火车站周边被骗、被偷、被抢的经历。但是你放心,我们晚上这些出来拉客的都是做正经生意的,白天那些拉客的年轻女子,穿金戴银的,样子凶巴巴的,都是干坏事的。”
基于此,张阿妹的不少生意都来自于回头客。但凡有男客人来住店,张阿妹都要反复叮嘱:“不要出去乱搞。”客人们自然也心知肚明。
有一天,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顾客愁眉苦脸地回来,说兜里的1000多元钱都被偷了,想问张阿妹借银行卡,以便家人打钱过来。“我问他是不是出去乱搞了,他说:‘不是,昨天过来你就说了不要出去乱搞,我怎么会去呢?我的钱是在火车站排队买票时被掏了。’幸好他另一个兜里揣着三十块零钱,要不吃饭的钱都没有。”
张阿妹之所以反复提醒客人,是因为有些色抢团伙盘踞在部分旅店里。做正当生意的人对这些人避之唯恐不及,如果跟这些人扯上关系,旅店生意就会大受影响。
七
昆明这个城市到底安不安全?
生活在这里和旅途经过这里的人们无法否认,“3·01”事件后,人们偶尔会冒出这个疑问。
针对市民的安全感问题,都市时报记者曾在5月发出100份调查问卷。据统计,受访的百位市民中,17%的市民感觉昆明不安全,对城市治安有些失望;80%的市民表示,“3·01”纯属偶然事件,且事发后,城市里四处都能见警,觉得“更安全了”;另有3%的市民认为社会太乱,只有从源头解决暴恐分子滋生的问题,城市才会真正安全。
5月的一个深夜,位于正义路的一家酒廊里,深情的英文歌挑拨着每一位客人的耳朵,40岁的高级调酒师夏绍昆在酒廊里接待客人。这是位调酒高手,酒瓶在他手中游离,不一会,一杯橙红相间的鸡尾酒就诞生了。”
这个初夏的夜晚,27岁的昆明人小戴与女友再次到酒廊消遣。按照小戴往常的口味,夏绍昆调了一杯他最爱的“大炮”(一种以威士忌为主要调酒的鸡尾酒)。小戴在昆明做建筑工程,工作中少不了应酬。“一周7天,4天在应酬,2天在酒吧,还有一天在家休息。”
小戴并不认为两个多月前的事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3·01)第二天晚上我就出来了,个别事件说明不了什么。那晚路上人虽然很少,但我觉得很安全,我身边认识的人都很正常。”他笑道,“我大学是在外省读的,学校边晚上经常有人打架,那些地方才叫没有安感。”
对于“安全感”,小戴有自己独特的解读。“昆明非常适合生活,很平静,离开昆明超过一个星期,我就会没有安全感。”他窝在沙发里,抿了一小口酒,女友静静倚在他的肩头。
在灯红酒绿的世界之外,陈宇贵依然在火车站前徘徊。老板娘虽然去意初显,虽然自己的生意确实清淡,但陈宇贵还是决定继续干下去。
“听说火车站要搬到呈贡,那时候我就回去。我肯定要回去的嘛!”他甩出一句重庆话。
张阿妹说,她终究也是要回四川的。“等这里都拆迁完了,我就回去。老家还有点田地。”她喜欢昆明,却在昆明“最复杂”的一片天地里度过了一段大好的时光,其中的恩怨,只有她自己最明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个别人物为化名)
都市时报刘晶晶实习记者高晨曦见习记者孙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