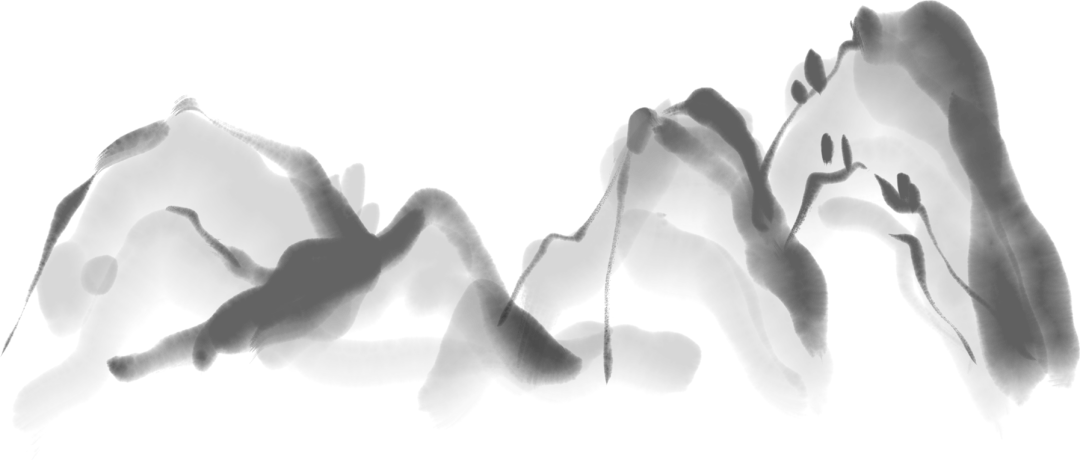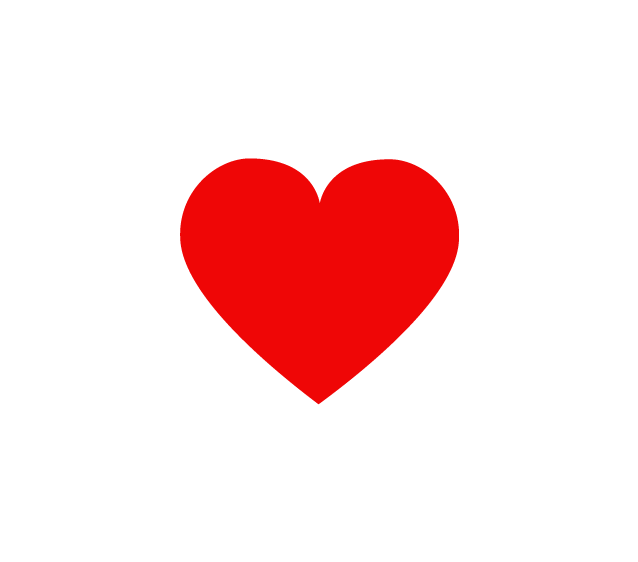水潭村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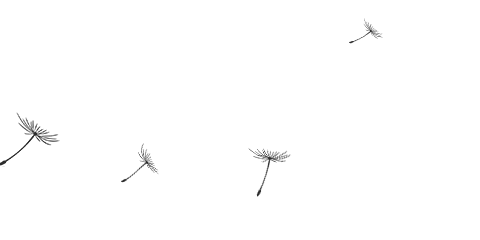

水潭村紧邻永昌堡,与抗倭城堡隔河而望。水潭的地形很像长方形,长方形的三条边(即三条河道)将村子框住,故有古名“水团”,被水团团围住之意。在数百年前,水潭村也是可以望见大海的,这个龙湾平原腹地靠近东海岸的小村子,因田地有限,成了龙湾唯一一个世代以打渔为生的村子。

水潭村轶事
文 / 王乐天
水潭,原名“水团”,因村落地势低,属水网平原,又被上横河、下城河、水潭河等众多河道团团包围而得名,后易名为“水潭”,一直沿用至今。水潭村的二个农业小队属永兴康二村管辖,系世代以捕鱼为主业的渔村,渔业为该村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水潭村人口稠密,村民大多系殿前李浦王氏后裔,他们之间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彼时,村庄所有房屋皆坐北朝南,面向宽阔清澈的水潭河枕水而居,站在自家的阳台、门口,皆可闻河水气息,连睡觉也都听得见水声。

我对水潭村的最初印象,来自孩提时代。当时,去一趟位于下垟街的外婆家,从我家所在的新城村出发,要依次途经城南村、虹桥村,过虹桥村后,得走上很长时间的田野小径,再过萼芳村,才能抵达外婆家。而在这条漫长的田野小径,除西侧稀疏地分布着几间落地房外,广袤的田野皆为绿色葱茏的庄稼地,春秋遍植水稻,冬季种上小麦,从这里往西远眺,隔着河道,远远可以看到对岸水潭村鳞次栉比的房屋及整齐有序地泊在岸边的一排排小渔船(大的渔船停泊在蓝田浦口的专用码头)。

▲水潭河
第一次真正走进水潭村,是在1978年的初夏。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南门街1号的徐龙家乔迁新居至水潭村,邀请我们老邻居一行人去他家作客。时过境迁,去他家玩的细节我已遗忘殆尽,但对当时去他家的水上运输工具渡船儿仍存有非常清晰的印记。他家自建的新房位于水潭村的最西端,而村里唯一的桥梁系横跨在最东端的望海古桥。虽然直线距离很短,但如果步行,则需要绕上一个大来回,我们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在水潭村的中段位置的简易渡口坐渡船儿过河。

▲水潭河边的河埠头
渡船的木质船体呈四方形,无浆、橹,两边用长绳固定在两岸桩上,外表被涂上紫色的桐油漆。渡船儿是水潭村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沟通水乡两岸的“移动桥梁”,可以起到以船代桥的功用。平时,它便成为水潭村村民们外出办事、走亲访友、孩子们上学、放学等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当然,渡船儿也有其缺陷,要是遇上大风或者雾大能见度低的天气,就要停走,只有等风停雾散后,方可复行,否则就会有生命之虞。
那时,渡船儿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公共设施,它不需要艄公,不收船钱,解缆后随到随走。平时,如果没有摆渡的人,这只无人看管、两端系有缆绳的渡船儿便随意飘荡在河面。当时,我们赶到简易渡口时,渡船儿刚刚载着一群人走向对岸,于是,大家只能耐心地等待上一拔人靠岸后,方拉回渡船儿。一上船,颇有新奇感的我们都争先恐后去拉盘在船头的粗缆绳。渡船启动时,在碧绿的河面上走动起来,一会儿,船体便开始平稳地走到河中央,直至摆渡到对岸。

▲永梅公路上的水潭村,横垮水潭河,
始建于1986年,长度42米。
上岸后,一股强烈的鱼腥味气息扑鼻而来,渔村气息呈现无疑。低矮错落的建筑物上有着醒目的政治标语,三三二二的妇女步履不乱地走下台阶,蹲在大小不一的河埠头淘米洗菜濯衣。岸边散落着多棵百年以上的古榕树,沧桑的树身刻满着岁月的痕迹。榕树树体庞大,枝茂叶繁,根系紧贴地面,瀑布似地张开,浮雕似地凸起,浓厚交错的深绿色树冠更是严严实实遮蔽了头顶的苍穹。古榕中,有的二三人方能合抱,有的俯身下去接近河面,点缀于碧波涟漪的河面,一派江南水乡的韵味。榕树下,聚集的村民在悠然地下棋、打牌、聊天,显然,他们生活的节奏是缓慢的。那次的一趟渡船儿的水上之旅,虽然时间短促,但与我而言,显得既兴奋又刺激。如今,渡船儿头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偏僻地区的个别风景区里,偶尔还能看到它的身影。


▲水潭路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数棵百年榕树,枝叶荫翳如盖,是村民 平时乘凉,休憩的好去处。
水潭村的孩子,就是典型的“我家就在岸上住”的孩子。在水潭村,游泳是每位村民的基本生存技能,每人均与水结下不解之缘,无论男女,人人皆有一副好水性。几岁的孩子也会下河,关键是在呛过几口水后,便能够无师自通。一俟夏日,水潭河就成为整个村庄的天然浴场,大人、孩子一齐在河里戏水游泳,热闹异常。宽敞的水潭河水质清澈,鱼类丰富,白天里,沿河到处都有垂钓的人,钓艺好的人经常可以为家里增添一道美味。到了黄昏时分,轻晃慢漾的河水,波光粼粼。几只小渔船闲散地泊在河中,两侧站着几只训练有素的鸬鹚,脖子上都套了环,扑闪着一对大大的黑色翅膀。一旦发现水中有鱼,主人便用长长的竹篙把一群鸬鹚“扑哧”一声赶下河,鸬鹚们争先恐后地跃入水中,上下翻飞。一会儿,宽大而尖尖的喙,便会叼着挣扎的鱼儿露出水面。鱼儿吐给主人后,主人便扔进一旁的鱼篓。台风天过后,河水浑涨,河中除了放排的,岸边也少不了也有人支着扳罾网,他们徐徐将网收起,又缓缓放入水中,一收一放,宛如一幅图画悬挂眼前。

▲眺山桥,位于水潭村的西首上汇头,由村民集资上百万元,始建于1982年,与东首的望海桥形成“山海呼应,古今合壁” 之势。建桥前,村民大多通过水潭河上的渡船儿出行。
每年的鱼汛期间,水潭村的男人们几乎全部出海捕捞。渔民这个与大海密不可分的职业,平时同家人聚少离多。而在驾驶小船的年代,每次出海作业都是险象环生,遇上海难、蹚上海险是习以为常的事。因此,于他们而言,人人都有着渔事信仰和海上禁忌。而逢休渔期,他们又将抠螺蛳作为家庭的副业,并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其足迹遍布龙湾境区野外及各条河道,每天早出晚归,随身准备足一天的干粮和水,这样,整天下来,总能满载而归,马上就有小商贩争先恐后地来收购,并送到附近的菜市场里去售卖以贴补家用。由于他们所抠的螺蛳特别新鲜,而且价格便宜,因此很受人们的欢迎。



▲位于虹桥与一条无名小桥之间的白水粮站,系当时永强地区四大粮站之一,规模仅次于永中粮站。
去水潭村的路上,还有一处景物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介于虹桥村的虹桥与横垮在横河桥上的一座无名小桥之间的一座粮站——白水粮站。粮站是我自小习见的景物之一,它位于李浦河、水潭河与大塘河三河交汇之处,东北面分布着一排弧形的河埠头,并有着高高的石阶。作为当时龙湾地区的四大粮站之一,其规模仅次于永中粮站。粮站是国家计划经济下特有的产物,是当年红火的单位,与老百姓的生活须臾不相离。当时,某一户人家若和粮站有密切的关联,那么他家就会引来太多艳羡的目光。在我的少年记忆中,几次夏收征粮中,由于人手缺乏,父亲曾临时被抽调到白水粮站,做过短期的粮食助征员工作。
粮站的院墙上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火”“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等排刷黑边红字标语。当时,粮站高二层,其间散落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粮仓和几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晒谷坪,楼顶则是用水泥浇成的大平台。记得九十年代初期,气功开始在社会上如火如荼,这股前所未有的热潮也迅速风靡了中华大地乃至偏僻的乡村。家乡的教办曾邀请温籍著名气功师林秀权先生举办过几期铜钟气功学习班,地点就设在白水粮站二楼楼顶的大平台上,我的父母随其他教师曾一道报名参加了培训班。上大学期间,经母亲的牵线搭桥,我有缘结识了林秀权先生,从此,引导我走上了与气功相伴的漫长道路。从这个平台俯瞰,三条河流紧密包围着粮站,河面开阔,水质清澈,往来的船只络绎不绝。


▲虹桥,又称东引桥,始建于崇祯四年(1631年),与白水粮站仅有百米之距。
小时候,我曾与父亲多次去过粮站送过公粮的经历,年年雷打不动,基本上是父亲借用邻居家的小划船,从家中出发,一直划到粮站前的河埠头。到了粮站,因为人多混杂,场面显得热烈壮观。缴公粮时,质量检验是第一关,兹事体大。等候质检评判的时候,远道而来的乡亲们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队,能不能过关,这自然少不了还得看质检工那张阴沉不定的脸。顺利的话,抽检质量合格,过磅后,还得自己扛着那一袋袋粮食,在管库员的不断催促下,费劲地倾倒在越来越高的粮仓里。那时的粮仓像大山一样高耸着,倾倒下来的几袋粮食,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一年一度的统购任务才算大功告成。
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交公粮不顺的时候,比如抽捡质量不合格,要么水分比例过重,要么杂质过多,就被要求挑到旁边的晒谷坪里重晒或用风车将秕谷灰尘吹走,用筛子筛净再重新过磅。如果天气不好,工作人员就要求他们拉回家,改日再来。遇到这样的事情,乡亲们自然极不情愿,一路牢骚通天,有的乡亲执拗,便会开始无理取闹,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的争执。
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及粮油棉征购任务,延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就此作古。从此,交公粮成为一个时代的背影。每年夏、秋二季,排着长队到粮站卖粮油的场景渐行渐远。粮站,从当初的门庭若市渐至门可罗雀。又经过几轮乡镇合并以及粮食系统的机构改革后,粮站不再对外营业。如今,白水粮站肌理尚存,但已形同虚设,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而我的父辈们则成为白水粮站荣辱兴衰的直接见证人。

▲白水粮站前的无名小桥
粮站边是一座狭窄陡峭的石桥,那是当时通往永兴的必经之桥,虽然两边安装了护栏,但人行走在上面,透过桥石间宽大的缝隙,看着下面水流湍急和宽阔的河面,还是显得胆战心惊。每次,我都要屏住气息,把心放在喉咙里,并小心翼翼手扶护栏,不敢往河里看,只有一步一步地挪到陡坡的底部,才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那个水运昌隆的年代,人们远行与运输货物大都依赖水上船只。横塘河的河面上,总有南来北往的客船、农用船、货船及船帮吃水甚低的驳船等各式各样的运输船只在人们的视野里穿梭往来,一派繁忙景象。运输船只有机动的,尾部发出低低的轰鸣,更多的是单桨手划的,俨然如现时的马路那么热闹。
去水潭村次数日益稠密,是在我上了高中以后。在永强中学就读期间,我的一位同班同学王进龙就来自于水潭村,从那时开始,我们之间就缔结了深厚的感情,并延续至今。王进龙个头不高,内敛少言,一脸青春痘。那时,大学实行精英教育,录取率低,只有极少数人从高考中突围,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愿望,幸运迈入了遥不可及的象牙塔大门。而大部分的同学则铩羽而归,只得选择来年的复读班或走上学习手艺的道路。高中毕业后,我和他在求学轨迹上分道扬镳,我上了当地一所普通高校。王进龙选择了学习机械手艺,学徒出师后,便自立门户,像一位孤胆英雄,毅然开启了一条茫茫的自主创业道路,创办了一家小型的阀门厂,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并和这份工作死磕到底。我曾多次参观过他的厂房,绕过他家前门,再经别人家的后门拐弯往里走,厂房里面光线幽暗,几台铣床、磨床、机床一字排开,整日机器轰鸣,电光闪烁。王进龙给我讲解过关于阀门制造的种种工艺流程,听得在机械方面属完全门外汉的我一头雾水。


▲水潭村上的古建筑怀清堂及环海桥
分离是生命的常态。尽管我们暂时分开,可这一切并没有切断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上大学后的寒暑假里乃至参加工作后很长时间的一些周末,我都会去他家“点卯”,王进龙都会忙里偷闲跟我扯上一番话。之后,随着永梅公路的通车和永安路的落成,更加拉近我家与他家的距离。当时,出他家的后门,便是高中数学老师王汉旺的家。虽然高中时代我所在的班级没有排过他的课,但王进龙的弟弟却曾受惠于他的教育。王老师是学生们心目中众口一词的好老师,他在课堂上讲解条分缕析,富有逻辑,每一道的数学题的解答都宛若打开了一扇门,令学生们感到豁然开朗。可在学校,王老师的名声并不是来自他优秀的教学水平,而是出于他的业余爱好——武术。王老师擅长散打,系当地武术组织金水门组织的重要成员。据说金水门拳法是流传在浙南的民间武术,创立于明代嘉靖年间,其主要内容有“金、木、水、火、土”五组攻防技法,还有两个套路与功法练习。其特点是突出武术技击广泛,多以两人合练武术。那时在永强一带,拥有 “Fans” 无数,向他求教者亦络绎不绝,还常被一些单位邀请去执教武术,亦在学生中广收门徒。不久,王老师便调往当地的公安系统,从此走上从政之路,并辗转了不少部门。他在仕途一直很顺利,先后担任瞿溪派出所所长、区经信局副局长、区安监局局长、书记之职,并在区政法委副书记任上退居二线。

▲王进龙老家
当时,王进龙家位于水潭村西岸的东面,系三间两层落地房,从他家举目就能望见近在咫尺的环海桥(又名十二间桥,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现已标牌予以保护。因从此行走不便,在印象中,我仅有一二次涉足过环海桥。)以及与之相辉映的怀清堂和二圣庙等二座水潭村最具特色的古建筑。王进龙家兄妹四人,他排老三,弟弟王儒洲系我大学的学弟,就读机电工程专业,毕业后,便选择了去家乡的沙城中学任教,并一直坚守三尺讲台至今。爱读书的他,时不时与我在市图书馆邂逅。每次去他家,都会受到王进龙热情的接待,我们之间相谈甚欢,简直无话不说。他有时也会向我大倒苦水,诉说个体办厂的艰辛。作为经营着一家在种种夹缝中生存的小微企业,利润微薄,他总是羡慕我在一家树大根深的国有单位享受着一份枝叶丰茂的俸禄,衣食无忧,生活无虑。前些年的一个周末,我尽地主之谊,邀请了一群朋友去故乡永昌堡观光旅游,当天,王进龙开着自己的私家车,热情作陪了我们一整天,他乐于助人的古道热肠使朋友们深受感动。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王进龙在事业发展一帆风顺,可他的爱情却像一穗秕谷一样颗粒无收,直至近不惑之年才如梦初醒,奋起直追,停下浪游的步伐,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收获一份姗姗来迟的爱情。在家人的反复动员和亲友们的大力撮合下,终于做了婚姻的奴仆,实现独身主义的巨大转变。他将这一喜讯在第一时间与我分享,还特携未婚妻在温州市区的一家酒店里专门宴请了我全家。她的未婚妻来自平阳南麂岛,性情直爽,善解人意,属能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型,我为他找到一份真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结婚后,王进龙便搬迁至水潭树南岸书院东路自建的四层联建房,新家被她爱人打理得井井有条。如今,王进龙有了两位可爱的儿子,乖巧聪明,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他和爱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未来抱有很高的期许。近几年来,我们虽然联系不多,只是在微信上保持着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疏淡,却互相洞悉对方的讯息,我们大约属于无言但却彼此信赖的人。


▲水潭路及其弄堂
在水潭村,还住着另一位同学王进湖,他们两家离得并不远,虽然高中阶段,我和王进湖不在同一个班级(他在另一个理科班)。但出于一个共同的业余爱好——书法,我们很快结识起来。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聊起书法,他总是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记忆犹新的一个细节是,他的裤腰总是挂着叮叮当当的一大串钥匙。当时,王进湖瘦高,与我同属典型的豆芽型,平时讲话慢条斯里。高二时,在语文老师陈小平先生的倡议下,学校曾经举办过一次师生书法展,已在书法初露端倪的我兴致正浓,不知天高地厚地竟然书写了五种书体去参展,数量最多,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此次书法展的主角。其中,临摹欧阳询《九成宫》的楷书作品还被校方鼎力举荐参加温州市临书大赛,并获最高奖,在学校中哄动一时,由此名声大噪。而王进湖以一幅优雅的蝇头小楷入选,同样引人瞩目。当时,学校特地邀请了当时瓯海两位知名书画家吴明哲、吴佐仁开设书画讲座,那天下课后,同学们都争相去教室占座。吴佐仁先生讲授作画的技法后,当场在黑板上现场演示山水画创作,当时,在我们看来,吴佐仁先生的画几乎可以假乱真石涛式的画。先生一画毕,同学们便纷涌而上,争先恐后讨要作品进行收藏,他的现场画作顿时成为当日的抢手货。而吴明哲先生的大篆及甲骨文的书法外拙内秀,独辟蹊径,而不入俗格,作品的曲高和寡一直无人问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却被王进湖如获至宝地保存起来。现在这些细节回忆起来仍然津津乐道。因高中期间,我已能以书法作品入展而浪得的虚名,从而给我带来一道亮丽的光环。至今,仍有高中同学不时向我讨取“墨宝”,使我深感惭愧,限于天赋,性情慵懒,没有心境沉潜下来,并缺乏一以贯之的钟情,我的书法水平依然原地踏步。

高中毕业后,我和王进湖渐失联系,只是后来在王进龙家曾经邂逅过一次,岁月不饶人,原先一脸青涩、一个生活门外汉的王进湖进入中年后,容貌变化非常大。尽管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皮鞋一尘不染,但饱经沧桑的他已明显开始发福,只能用朋友圈里面的自潮来形容:你好,油腻大叔。这正如丰子恺先生在《渐》这篇文章里说过:“变更是渐进的......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也许时光的变迁是永远不可变更的定律。我们久未见面,我想同他说点什么,但又一时半儿找不到切入口,显得有点尴尬。之后,便是在同学们罗生门式的片断叙述中,陆陆续续地得到他零星的消息,我把它们串联起来,仿佛一部一个个片段串成的记录电影,内容或与事实有些出入,但相信出入不大,他大多数的时间长期扎根在家乡,并频繁更换了不少职业,如今,他经营着一家五金店并兼卖桶装矿泉水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但依然保持着书法艺术的浓厚兴致,虽然在时间的占有度上,书法只是他很小的一部分。而在我的印象之中,王进湖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每论及社会上存在的诸多不公正现象,他总是言辞犀利,大加挞伐。

▲水潭村及村民公约
时光总是抛下一些无法割舍的往事兀自运行,随着轰然到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水路衰落,航运骤减。而水潭村从事渔业的村民已廖廖无几,大多数早就另谋出路。如今,水潭村,这个颇具诗意名字的村庄,江南水乡的最初原貌荡然无存,早已不复“去年天气旧亭台”,沧海桑田,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