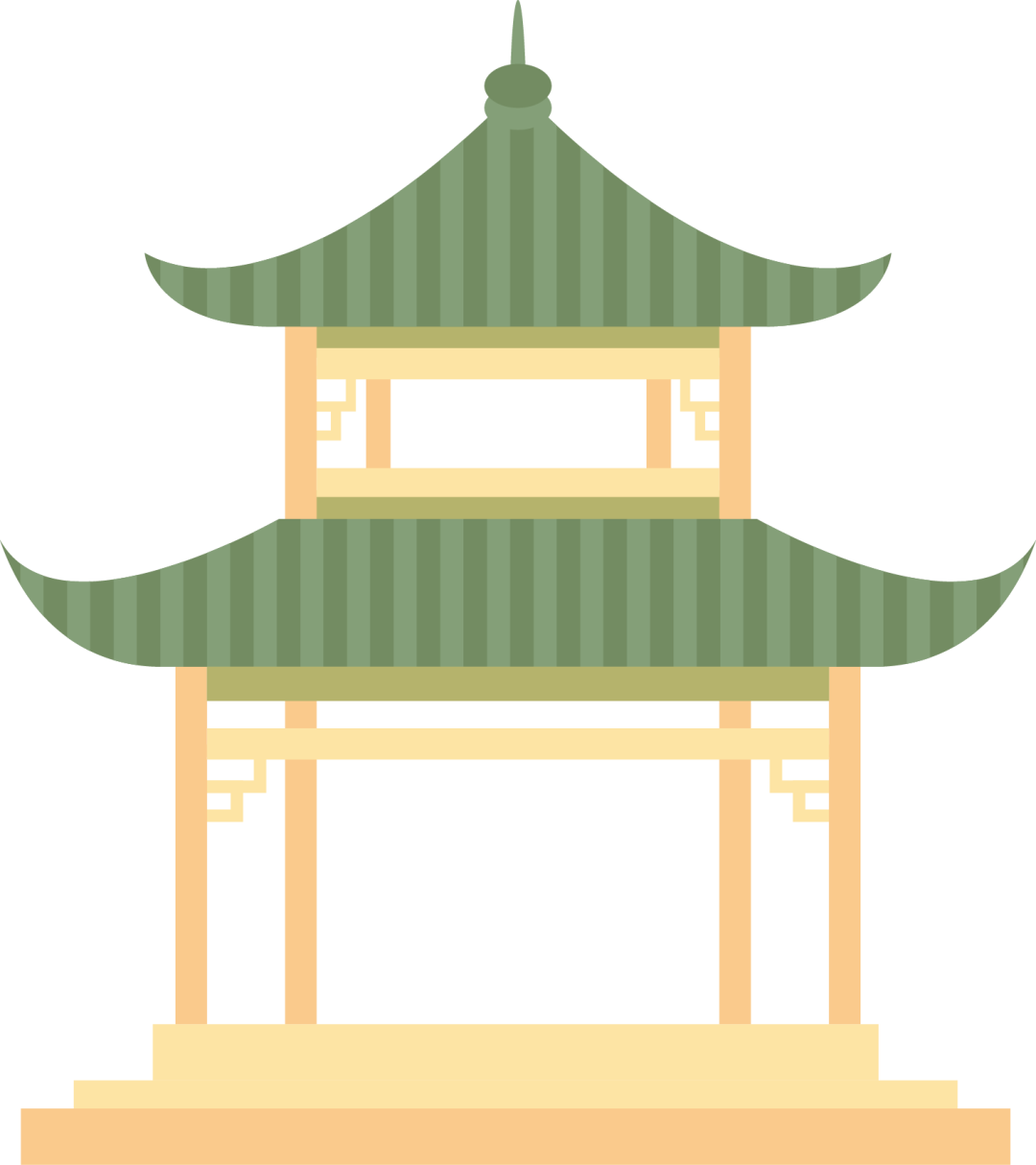南门街




编者按
“南门街起于永昌堡的南门迎川楼,至城南村的浬浦桥止,街道呈南北走向,它是白水乡政府通往南片几个下辖自然村的唯一交通要道。当时,街面店铺林立,道路虽狭窄但不失繁华,行人要完整地穿越长约二百米的南门街,往往得花上四五分钟的时间。”

南门街
文 / 王乐天
上小学的五年,我每天要从南门街上来回往返四次,消磨在这条道路上的时间,仅次于老家所居住的弄堂状元里。
▲南门街最北端,永昌堡南门:迎川楼。
迎川楼的入口,一间乡村诊所赫然在目,诊所坐西朝东,分上下两层,一楼外间为诊室,里间为药房兼注射室,二层阁楼则作为卧室。开设这家诊所系一位五十多岁的单身中年男人,他是周边一带妇孺皆知的人物。当时,在乡村有句流行语是“一是听诊器,二是方向盘”。医生在最吃香的行业里名列榜首,因此,在找对象上就占了先决条件,可他却一直没有结婚,令人迷惑不解。
尽管与乡卫生院近在咫尺,但他的诊所里总是人满为患,每天聚集着慕名而来的患者。诊室的墙壁挂着多面大红锦旗,上书“妙手仁心”“当代神医”“再世华佗”等字样,这些是对他医术精湛的最好证明。在我出生以前,男人就已经开始在这里行医,应属扎根长久的“赤脚医生”。诊室里总是散发出特有的苏打水味道。穿着白大褂的他,对每位患者都诊查细心,不紧不慢地把脉、测体温、翻着病人的眼皮,查看舌苔,并熟练地将听诊器套上耳朵,把拾音部分摁到病人的胸脯上,镇定而严肃地询问。而后,他取下听诊器,用余温尚存的手拧开笔套,在诊断桌的便笺上奋笔书写着药方,再去药房取药、配药。
▲南门街
他的打针也颇见水平,打针时手轻针准,他一边撩开孩子屁股外的衣服,一边将蘸过紫药水的冰凉消毒棉签在紫红的屁股上来回擦拭,敲开针剂的瓶盖,将针管伸进去把药水抽进注射器,并迅速将炫亮的针头刺进粉红色的肉体。当母亲怀抱里的孩子还来不及哭泣时,他已经将针管从屁股里了拔出来。
平时,他的桌上总是摆放着一个棕色的出诊箱、一台血压计以及整齐摞着一些医学书籍,一本人体解剖学已经书页翻卷,封面残缺不整,里面画着许多红蓝圈圈、线条。他能看各种各样的杂病,虽然他并无把握处理那些难度稍大的病症,他完全是出于对医学的好奇而自学成才的。
关于他的另一重记忆,则是他一次驱贼的传奇经历。某个深夜,两位惯偷撬开了诊所的大门,顺着楼梯欲摸向二楼的卧室。被脚步声惊醒的医师显得很淡定,他并没有大声地喊叫,也没有准备捉他个现行,而是镇定地打开两个热水瓶,拨掉瓶塞,将两个竹蔑外壳的滚烫热水瓶顺着嘎吱作响、漆皮剥落的木楼梯一路滚下来,小偷被热水瓶在地上炸碎的声音当场吓得仓惶而逃,从此再也不敢光临诊所。十几年前,医生因病亡故,这家诊所也就不复存在了。
▲条件简陋的南门街理发店,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紧挨着诊所的是一家理发铺,由两兄弟共同经营的,哥哥碎奶,弟弟钟辉,他的儿子阿海与我同天出生,后来也子承父业,如今,在附近的迎川路经营着另一家理发店,他们家就居住在与理发店近在咫尺的南门街一幢二进的后进院子。当时,它是周边几个自然村唯一的一家理发店。店铺一面临街,一面枕河,占地面积不大,仅有十来个平米左右,店门口没有花里花哨的招牌,里面设施也十分简陋:二把理发椅子、二面镜子、几条木制的长凳紧靠在东面的门口,墙壁上张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老年历。而因为绝佳的地理位置,加上俩位师傅勤快和手艺好,从早到晚,店堂里总是熙熙攘攘的。
一年之中,他们从不放假,恪守手艺为生计为本的师训,每天天蒙蒙亮准时开门,这种坚硬而又坚韧的习惯持续了数十年。他们来到店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爿爿灰旧的木门板卸下来,按照各排板上的数字标识有序地叠放在墙角。卸下所有门板后,整个店堂也就一览无余。然后,他们开始装煤球炉、烧开水、扫地,待最后打扫好店内的卫生,两位理发师便开始坐在靠门边的长凳上,静候顾客的光临。晚上店里打烊后,他们又将背面写有“南一南二”等标记的木门板一爿爿地再嵌入门框上下的木轨槽,按次序重新装回去。
▲横跨南门河,连接南门街与庙上路的古桥:凝秀桥。
两位师傅们招呼客人入座时,便会先取下搭在肩胛上的白毛巾,轻轻掸干净椅座上残存的碎头发。待客人坐定后,他们会甩动一下围布,顺势不紧不松地围在客人的脖子,系好后,便在拿起推剪里滴上几滴机油,在耳边试听一下声音是否正常,剃头的序曲才告完成。
这家理发店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理发师为顾客洗头的方式。理发店用一堵墙隔开,南边的是它的工作间,北向的小屋专门用来为顾客洗头,小屋的西面开了一扇小窗,从窗口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河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小屋里,十来只竹壳热水瓶并排放置在地面上,还有一口盛满清水的大水缸。在没燃气和热水器的年代,理发店离不开炉子,是完全靠煤球炉烧开水。一只煤球炉子一刻不停地烧着开水,旁边堆着黑乎乎的煤球。烧水的小屋子时常弥漫着白雾似的水蒸汽,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洗头时,师傅提着烧开的那壶沸水,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把沸水和冷水互掺着灌进自制的土水箱里,待差不多调试好水温后,便拧开龙头,开始放水为顾客洗头。顾客系着沾满发屑的围布,坐在空间狭小的洗头处,面对洗头槽,低头弯腰,任由理发师用一块泡得松软的肥皂,慢慢地清洗。因水温是没有办法调节,全靠师傅的经验,有时烫一点,有时冷一点,顾客们也没有什么会埋怨的。
在相当长的年头,我都是这家理发店的顾客,因为它离我家仅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路程。可每次我去理发店,父母总是很伤脑筋,坐在那张可以转动的坐椅上,小时候,淘气的我总不那么安分,似乎不肯轻易就范,在位置上不停地闹腾着,不愿理发。于是,父母也得经常上去与师傅一道,在后面共同摁住我,随着电推子嗡嗡的声音,才艰难地为我完成理发。如今,这家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理发老店仍然倔强地生存着,由碎奶师傅的唯一儿子接手下来。
过理发店,一路往南,它的中段开始日趋热闹。这里铺排着众多的临街店铺,均坐东朝西:杂货店、水果店、刻字店、草药店、五金店、裁缝铺、乡供销社的副食品门市部以及简陋的马路菜场,门口一律对着并不宽敞的南门河。
众多的店铺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家裁缝铺了。于我而言,它是一家趣味无穷的手工作坊。与其说是裁缝铺,其实不过是一间狭长的面街店面而已,由夫妻俩共同经营,墙上、挂钩上悬满了布匹和成衣。两台缝纫机一前一后地安放在一楼的前屋,合奏出二重唱。一进裁缝铺,总是散发出缝纫机油好闻的气味,常见男人将笨拙的老式熨斗,抓在手里,在布料上梭过来梭过去。裁缝铺的后屋为厨房间,从前屋登梯而上为卧室。在那个循规蹈矩的七八十年代乡村,商品服装几乎没有创造力,平时,乡村的孩子总是习以为常地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当时,很少有人家去买成衣,只有到了腊月天,大多数人家才凭票证去供销社,剪来各色质地和花样的布匹,然后带家人到裁缝铺量体裁衣。旧时裁缝全靠手工,师傅的软皮尺往顾客身上左一拉右一扯,嘴里念叨着,量体后,他便拿出一个蔫巴巴的本子和圆球笔,记录下顾客的姓名、尺寸,并吩咐他们按期上门取衣。裁缝活时多时少,并不稳定,而每年将近年关时则是裁缝铺生意最为繁忙的日子:老老少少从头到脚的新衣需提前定做。夫妻俩就在房间里一直忙碌着,有时得连夜赶制。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男人担纲剪裁,他将布匹摊在长长的案板上,捏着粉色的划粉划划改改,并用尺子飞速打版,嘴里还不时自言几句,然后,开始咔哧咔哧地裁剪着布料。女人则围着围裙,戴着袖套,在默契地蹬缝纫机缝制衣服,于是,“哒哒哒”的声音一直回荡在小屋里。
简陋的马路菜场画面驳杂:一溜水鲜翠嫩的菜蔬担(这些都是自家菜园和自留地里种植的)、碎骨飞溅的肉墩、五颜六色的水果摊以及河鲜摊位上活蹦乱跳的鱼虾、拥挤又谐和地安处一地。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位面孔黑黝的女鱼贩,就仅用一根布交叉着,把孩子系在后背,既不耽搁买卖,也不耽误讨价还价。当然,平日里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会买上一些鱼肉,然后招摇过市。每天经过时,这里总是显得嘈杂脏乱,到处充斥着小贩的叫卖声与乡亲们的讨价还价声。当时,乡里几乎没有讲普通话的人,一种方言统治了这里的一切。在市价格涨落不定时刻里,一种基于方言的信任和亲近是必不可少的,在马路菜场中浮现的基本是一些熟悉的面孔,我特别喜欢这种方言与乡气交织而成的市声。在上学、放学两个时段里,马路菜场里总是人头攒动,每次我背着书包路过时,往往得侧着身子从一个又一个大小的缝隙间挤过去。
放学后,我时常会驻足在茶缸巷口马路菜场的一个摊位前,饶有兴致地看摊主炸新鲜的灯盏糕——铁锅里滚着深色的油,摊主随手抄起一个长柄铁勺,先浇上一层稠稠的面糊,然后往里面填萝卜丝、猪腿肉等内馅,有时也打一个蛋在里面,或者从盆里挑了只青色的大虾按在上面,而后再上面糊,放进油锅煎炸片刻。“嚓”一下,青虾很快变成红虾,弯身蹲在灯盏糕里。一会儿,色泽由黄转金色,慢慢脱离了模子,浮在沸腾的油锅里。摊主便手疾眼快地用一个铁柄漏勺将色泽金黄的成熟灯盏糕捞出,放在旁边的铁丝架上沥干油,等待售卖。有时,父母也会慷慨地买上一只犒劳我,那已是一种奢侈的奖赏。
▲南门街最北端的浬浦桥,过桥往南便是
原白水供销社所在地,现已成为东瓯王庙。
南门街南端尽头的浬浦桥是一条高陡而瘦削的石桥,这是一座有时间历史的桥梁。过去,除了走水路外,这座桥是连通南门街与红星小学以及南片诸村的唯一通道。在红星小学就读期间,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每天都要在桥上往返数次。它的南、北坡均由三块淡红色的长麻石条组成,中间由一根高高的宽阔石桥墩支撑着,桥面不到两尺来宽,但仅仅在东边安装了石护栏。每次行走在上面,看着桥石缝隙下面水流湍急,我都要屏住气息,把心放在喉咙里,显得胆战心惊,并小心翼翼手扶护栏,不敢往河里看,只有一步一步地挪到陡坡的底部,才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桥下的南门河面上,一天到晚,会有很多船只南来北往,有机动的,更多的是单桨手划的,有客运的,亦有货运的,来来往往,俨然如现时的马路那么热闹。一俟盛夏的晚上,石桥栏杆便成了乡亲们约定俗成的聚集点,到处坐满了消夏乘凉的人们,胆子大的,甚至敢四仰八叉地躺在并不宽阔的石栏上。凉风习习,驱散着一天的暑气。他们在昏暗的路灯下摇扇聊天,絮叨着一年的桑麻农事与家里长短,消夏会直到深夜,凉意渐渐上来,他们才起身回家,这已定格为我记忆中永远的风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石桥早已被改造成一条可以通汽车的宽阔公路桥,上面车来人往,热闹非凡。
▲南门街上的曾经的供销社副食品门市部,
现在墙面依稀可见“白水合作商店”六个大字。
据父亲说,祖父当年就居住在浬浦桥北面的第一幢老房子(南门街1号),而我的襁褓岁月——从出生到二三岁,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只是年代久远,我对居住在此的印象几乎全无。五十年代初期,祖父曾在一楼临街处经营着一家“王源来”苎麻店,店铺闻名遐迩,生意兴隆,直到实行公私合营后才停止营业,店面也充公了,从此,家道中落,风光不再,后来在此就相继开办过乡兽医站、供销社副食品分部。而二楼邻桥的两间房子则长期作为城南村委会的办公场所。
现在,房子已经显得破旧不堪了,一、二楼层之间的木质楼梯,人轻轻地踏在楼梯上,总会发出橐橐的声响。卧室的门是木头的,两扇门,向里开,一拉就“咿呀”作响。里面有几样不起眼的摆设,年代久远勉强支撑继续发挥出余热的衣柜、桌子、长木条做的椅子和一张嘎嘎作响的木床。虽然这幢历经沧桑的老房子被政府部门列入“危房”的行列,原先的另一户人家早已迁居水潭村,可四叔、四婶仍然坚守着在那里,不愿搬迁,成为老房子最后的守护者。